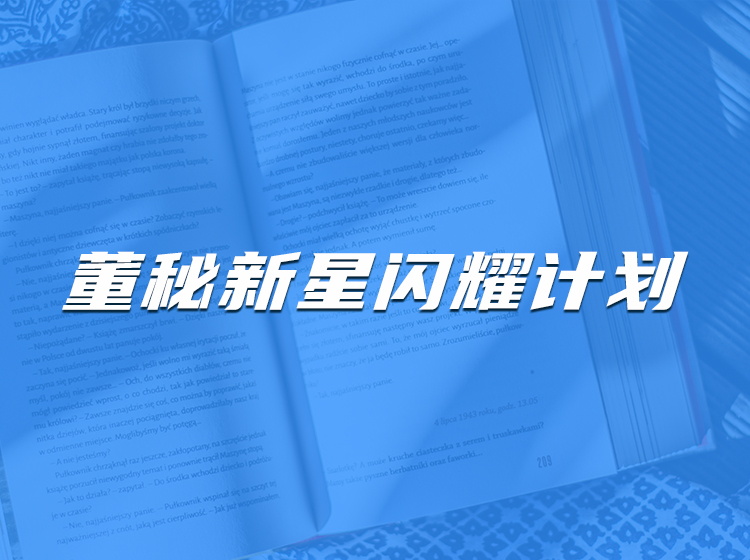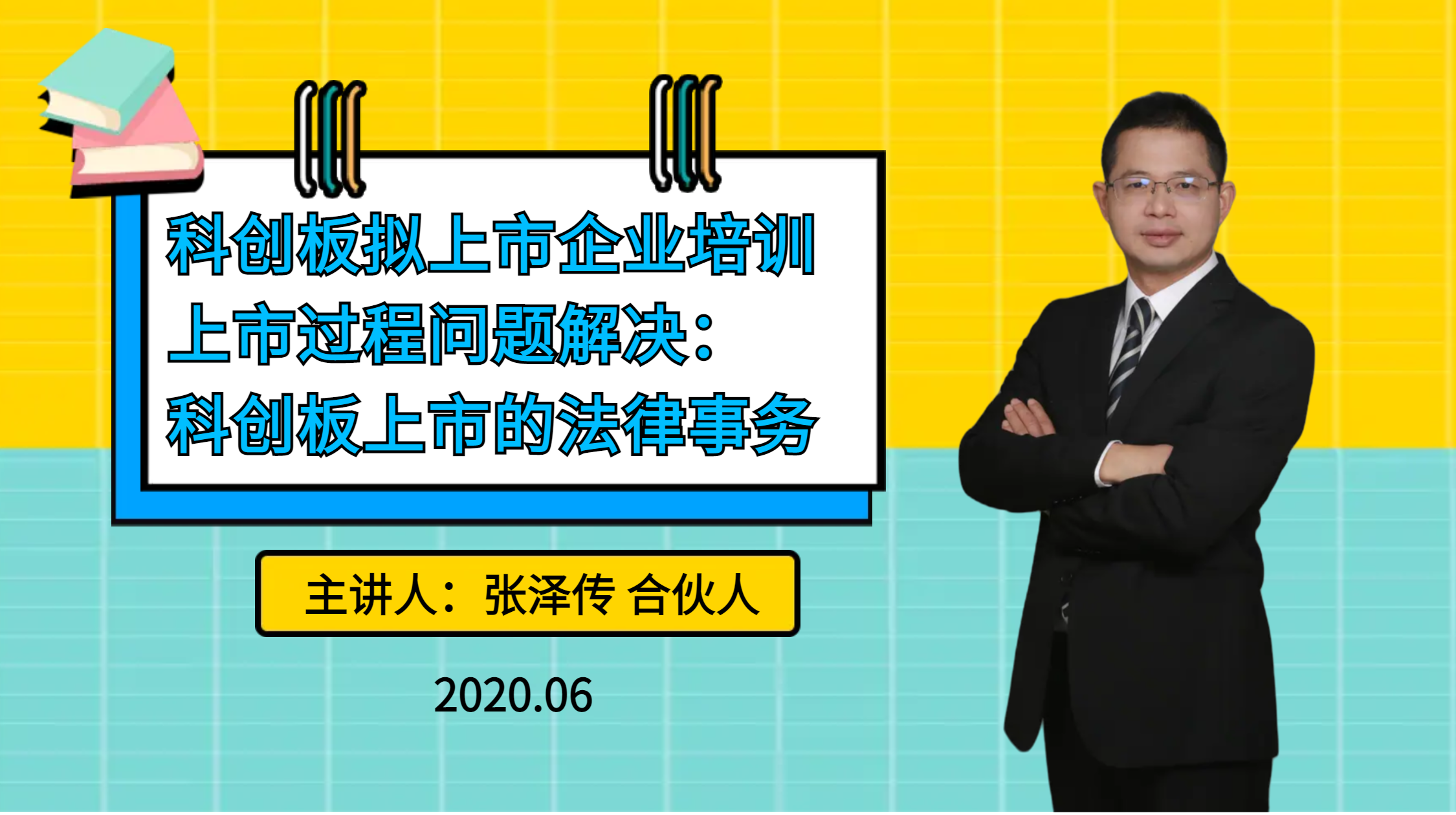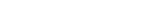本文为西京研究院发表的第726篇原创文章,赵建博士的第685篇原创文章。
现代货币是由信贷创造的,大头是广义货币即商业银行贷款创造的各项存款,小头是基础货币即中央银行再贷款创造的银行存款和现钞。每一分都是这样的创造,概莫能外。当然,一般个人和企业,除了现钞(央行“借条”)外,并没有资格与央行产生货币联系(无法在央行开设账户),大量的基础货币是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结汇和再贷款等创造的银行准备金。这样,作为中国金融业主导产业的商业银行,就成为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的桥梁,将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表联系到了一起。
但大部分人甚至是大部分经济学家没意识到现代货币和现代金融产业的重要性。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和文献学院派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货币面纱论,金融中性论,认为货币这个商品经济的“统治者”,金融这个现代经济的核心,竟然只是一层面纱,对真实经济的活动和均衡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然而这只是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其实最早源自费雪“债务通缩”思想,被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明斯基系统化总结成“内生不稳定理论”,被伯南克升华成“金融加速器理论”,又被日本学者辜朝明现身说法成“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一条主线,已经冲破学院派的形而上学禁锢,逐渐被业界和学术界认可。这条主线上虽然也有不同的视角,但有一条是相同:金融业是至关重要的,融资或债务活动会造成巨大的不稳定。我们姑且通俗的称这条思想主线为“费雪-明斯基-辜朝明诅咒”,或者叫“债务的诅咒”。类似“资源的诅咒”:债务既能带来发展,也可能会招致衰落,与资源型国家一样的命运。
这个诅咒的根源在于,金融业具有非常大的外部性,而且这个外部性具有两大特点:1,效果是不对称的,负的外部性远大于正的外部性;2,具有状态依赖性,在发生危机的状态,负的外部性大到不可思议。也基于这个诅咒,全世界的金融业都是高管制行业。即使是崇尚市场自由至上的欧美发达国家,最近几年也全力加大对金融业的监管。同时,强化了以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为主导的货币金融控制。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次贷危机后扩张了近5倍,疫情危机后不到一年扩大了近3倍,实际上就是强化货币的金融控制。
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金融产能最大的国家之一,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世界第一,当然其负债端生成的广义货币也是世界第一,甚至是美欧加起来的总和。中国的股市市值、保险资产也位列世界前茅。一个最典型的指标可以说明中国是金融大国,那就是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次贷危机后已经快速达到并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特别是疫情后的第一年2023年,第一季度金融业对GDP的贡献率竟然达到了13%,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金融业对GDP如此高的贡献率,在中国的高层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很可能是忧心忡忡的。无论是前三十年的工农兵建设国家的思维,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立国、实业兴邦的发展理念,都不可能容忍金融业如此高的增加值。去年中央多次重磅会议已经明确指出,在金融业发展方面,中国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监管要长牙带刺,要将严监管作为一种常态。高层已经很多年没有主动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相反一再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这意味着在总的认识坐标上反客为主,原来的“核心”变成了今天的“仆人”——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绑架实体经济。
18大以来,中国开始加大对两大“高污染”行业的治理:一是自然环境的污染,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进行整治,不惜拉闸限电、关厂走人;二是信用环境的污染,从影子银行、假借P2P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到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一直到体制内的商业银行。我们看最近的反腐,出问题最多的是金融行业的干部。
如果说十八大期间是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治理,那么十九大后,乃至延续到二十大后,防风险攻坚战都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实际上,一切进行的比我们想象的还早。自2016年开始,钢铁、煤炭等高耗能产业的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基本完成后,银行、第三方等作为高债务产业的金融业,在严监管的实施下也开始了供给侧改革。然而2016年房地产与地方债周期的再次崛起,延缓了总体上的金融去产能进程。由于对表外、第三方投资和财富管理公司的整肃,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利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特别是有利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这个跟钢铁煤炭行业是一个道理——行业集中度上升了,具有更高信用等级和隐性担保的国有金融机构当然竞争优势反而更大了。
但是2021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和通胀苗头,让旨在二十大之前解决各类深层次问题的高层下定决心彻底治理好房地产和地方债这两大顽疾。这意味着,自“三条红线”下发执行的那一天开始,金融去产能就真格的进入加速阶段了。但凡有点常识的业内人士就知道,房地产+地方债这哼哈二将产生的信用资产占据银行资产负债表多大的比例。一半?六成?七成?加上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数额之大、比例之高、风险之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如果不是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的,就根本没有如此程度的金融产能大跃进。为什么?因为根据经济学原理,一个企业扩大产能的唯一驱动力就是边际利润大于零,只要满足这个条件,扩大规模才是经济的、理性的,否则就是赔本赚吆喝,理性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因此如果净息差低于1.8%左右,银行就应该停止规模扩张,甚至为了减少损失要缩表。然而国有银行没有这样的硬约束,一方面它们的家底足够厚,可以摆布以前的利润来弥补净息差迅速收窄导致的利润亏损,以满足规模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是重要的货币政策执行和传导渠道,还承担着结构性货币政策等重大的社会使命,可以说是身不由己。
但是当高质量发展和战略定力,在一个债务周期的顶部坚持如此之久,债务塌缩引发的金融去产能就不可避免。我们看今年一季度上市银行的年报,在数据可以粉饰的情况下,绝大多数银行的利润增速都出现大幅下滑。即使如此,大量的利润也不是由信贷资产创造的,而是在投资端赚央妈的钱。央妈对商业银行这样的“资金空转”当然不满,行动上已经在长端国债制造了巨大的波动,让那些围绕着央行货币政策进行套利的银行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商行和农商行吃点苦头,让其知道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的存在,不能只进行单边一致交易,否则很容易发生像2023年美国硅谷银行事件那样的大风险。
与此同时,为了真正的降低资金成本,监管部门开始对手工补息等高息揽存打价格战的内卷行为进行整治,导致大量的银行存款流入其它金融产品,因为“价格自律机制”制定的银行存款利率太低了。负债端因为无法再高息养住存款,资产端又找不到合适的授信对象,说到底就是放不出贷款去,两端挤压,金融业去产能肯定会加速。在这种形势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速度严重放缓甚至是收缩也就不足为奇。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是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中枢,当银行资产负债表都开始收缩的时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加剧的。
4月份的社融和货币数据出炉,很多人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好几个数据都是创造历史的,M1同比增速除了2020年疫情刚发生的那一个月,自1986年有统计以来同比增速就没有为负数过。M2同比增速也破天荒的破8%,社融竟然出现萎缩。可以说一系列数据都基本上创造了历史新低。数据如此,当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负面的角度,中国的金融产能正在塌缩,持续下去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另一个是正面的角度,中国经济正在摆脱债务驱动和货币刺激的模式,正稳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在不依赖房地产和地方债的情况下,一季度GDP增速仍然能够达到5.3%。就像单位耗能的降低一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单位债务消耗也越来越低。这难道不是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吗?
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当然完全正确,但这只是形式逻辑和经济伦理逻辑,并非实践逻辑——实践操作中绝非风险清零或者既要又要还要,而是权衡利弊后的抉择。如果信贷和货币继续加速塌缩,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大。M1的负增长是极度令人担忧的,因为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除去2020年特殊的一个季度首次负增长。这意味着货币活力迅速下降,货币的社会动员能力大幅萎缩,也意味着债务通缩螺旋可能正在形成,如果不及时解开这个螺旋,货币收缩成为一种常态,通缩就会演变为一场萧条。这是1929年-1934年美国大萧条期间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费雪-明斯基-辜朝明们的债务诅咒,也是达里奥超级债务周期下行阶段惨烈的通缩型去杠杆过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逃不开债务的惩罚。那些滥发债务暂时还没出现不良后果的国家,只是一种暂时的滞后效应,甚至短期内还觉得无比繁荣——这难道不是吸食鸦片后的幻觉吗。就连美国这样自以为可以无限发债的货币霸权国家,都不得不吞下大通胀的苦果,更不用说其它资源动员范围有限的国家。拉美国家的MMT实验已经失败,越来越多的国家中了费雪-明斯基-辜朝明诅咒。
中国也会陷入这样的诅咒吗?我看未必。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是供给和需求都能承载当前的债务水平,也就是既能时间换空间,又能空间换时间。第二,中国具有足够的产能来规避通胀的威胁,实体经济还有一定的货币化空间。第三,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货币金融控制能力,不会允许金融机构像私人企业那样随意破产以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第四,中国具有防风险攻坚战的后发优势,从日本资产负债表大衰退到美国“两次大危机的比较”,中国具有足够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第五,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比较充足、币值还比较稳定、金融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备、金融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正在加速完善,能够抵御较大的外部冲击。第六,中国政府正在加快行动,最近制定的超长国债发行计划,说明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相对应的,央行的行动在后面可能会更加积极。
总之,4月份的社融和货币数据已经发出了可能要发生“大震”的强烈信号,政策层应该重视这一信号,及时行动未雨绸缪,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的优势,摆脱发达经济体曾经中过的债务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