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以及未来几十年,社会发展将以数字化技术向各行各业的深度渗透为特征,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与此相适应,源于工业时代的战略理论迎来一个重大变化,即企业不再被动适应环境,而是主动塑造环境。
企业与环境之间不再是机械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同演化。这时,可塑性,超脱具体行业,成为未来产业的共性。
产业可塑性源于若干确定的、普遍的长期趋势,包括数字化、模块化、服务化和融合化。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但也有着相对独立的内涵:
数字化(digitalisation)囊括了数字化(digitisation)、网络化和智能化三大阶段。这一历程在不同产业进展不同,料将持续较长时间。数字化带来全新的数字化资源,并改造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为价值创造注入新可能
模块化是一种处理复杂性的组织技术,将各种资源、功能、组织通过标准化接口相互连接,以形成更高级的系统。它在信息产业得到广泛应用,正在向传统产业渗透,如汽车。模块化是平台模式的基础,平台是通用性特别强的模块
服务化是指产品商业模式向服务商业模式的转换。更具体地,它强调卖家(供应商)与买家(客户)之间关系的变化,包括价值交付从有形的产品到无形的服务、货币交换从一次性购买到按需付费、客户关系从交易到持续互动
融合化是指原属不同主体的特征同时出现在一个主体。在我国政策话语下,产业融合主要体现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是对数字化、模块化、服务化成效的高度概括。产业融合对应的结果是用户体验融合
以上趋势将产业从某种给定结构变成了高度可塑的空间。产业结构可能仍然重要,但以洞察未来为己任的产业分析很难再从结构入手。
经典产业定义依归于最终产品。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需要重新思考的,恰恰是产品到底是什么?其实,产品只是价值的载体。在上述趋势作用下,企业完全可能以全新的方式创造价值和交付价值。新价值形态在与客户以及合作伙伴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迭代,进而又引入新的合作伙伴、新需求或新客户群体,形成新产业。
在上述条件下,产业价值创造越来越强调异质性、互补性价值模块的创造性混合,深刻地影响着产业经济性。工业时代的产业经济由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主导,而信息时代的产业经济由网络效应主导。
尽管不同行业的网络效应土壤各不相同,但网络价值在产品服务价值中占比将持续提升是产业共性。企业战略的增量和变量,也是重点和难点,就在于从一个边界模糊的产业空间创造性地识别、连接、整合这些价值模块,以实现更强的网络效应。
James Moore于199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提出生态概念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经典产业分析的不满。
在他看来,与其视企业为某个产业的一员,不如视其为一个横跨若干产业的生态的一员。他还认为,生态战略的着眼点,不是波特强调的价值链分析,而是不断创造新的价值链。
由此,Moore对两大波特概念,即产业和价值链,都提出异见。在产业融合范畴和深度远超三十年前的今天,生态战略毫不意外地深入人心。
战略本是资源配置的学问,默认前提是资源相对刚性。战略则强调资源整合和资源利用。
资源配置是指,把资源放在最能产出效益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产业、产品,可能是一个细分或区域市场,也可能是某个环节、某种活动
资源整合是指,资源配置之前,先审视资源整合的范畴,不局限于内部资源,而要考虑广阔的产业空间,尽可能整合外部资源。对应的生态现象包括战略联盟、开放平台、少数股权投资等等
资源利用是指,资源配置完成后,不仅着眼于现有价值链优化,更要充分挖掘现有生态资源的潜力,以其为踏脚石向新领域扩张。对应于所谓的无边界扩张
这意味着,生态战略是运动战,不是寻求一劳永逸的产业定位,也不是躺在核心能力的功劳簿上大梦春秋。这与产业空间的高可塑性有莫大关系。
环境的低可塑性,也即经典战略理论的假设,意味着给定资源范畴、给定资源利用方式的静态资源配置,很大程度上是零和游戏。
反之,高产业空间的可塑性,也即未来产业的一般特征,意味着有大量的互补性资源可能涌入,大量的新兴市场机遇可能被发掘,大量的价值形态可能会出现,为创新性资源整合和资源利用提供了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是动态资源配置,没有均衡,持续演化。
可见,产业可塑性是企业生态战略的基础假设。
产业界喜欢使用产业生态一词。本无不可,但容易与企业生态,即生态战略规划的对象混淆。
产业空间是企业生态的基础,但该空间并非某个企业的专属,即不存在所谓的“生态主”,因而不同于企业生态。企业生态需要不断从产业空间中整合资源才能维系自身存在,同时又对产业空间的权力分布施加影响力。最终呈现的产业形态,由若干交叉但不重合的企业生态在竞合中共同塑造。



 人才猎聘
人才猎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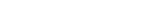


登录 后即可参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