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Peter Williamson和Arnoud De Meyer的新书Ecosystem Edge在斯坦福出版社出版。蒙Peter邮寄过来一些视频和文字链接,我下午花了些时间学习。有一些感想,回了他邮件。邮件不好说太多,记在这里可以延伸下
生态系统思维的一个重点是利用松散耦合的外部创新者。作为一种逆向思维,以我的观察,控制权和内部能力在生态系统环境中似乎同样重要。
生态学文献的最新发展反映了这一悖论。正如Adner(2017)总结的那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生态系统是一个价值创造概念。相比之下,Jacobides等(2018)的论文则声称协同专业化和基于标准的协调非常重要,更强调价值捕获的概念:从属关系。
在实践中也可以观察到这种悖论: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也许还有美国的巨头)正在同时成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和一个封闭的帝国。
很多人将Amazon云作为生态系统开放利用合作伙伴的案例,而另一些人则看到认为Amazon云基础架构来自其内部业务的积淀。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支付宝(蚂蚁金服),平安科技等。此外,生态系统之间的激烈竞争(例如,阿里巴巴与腾讯)可能会迫使“松耦合”的外部创新者站队,否则两头不讨好。
顺便说一句,有些喜欢说谁是做生态谁是做帝国,或者盟国什么的,都是话术——价值捕获以价值创造为前提、价值创造因价值捕获而持续,天经地义地需要两者得兼,什么帝国盟国生态的,没必要分出个高下。
操持这些话术的人也不真明白帝国、盟国、生态都是咋运作的,罗马帝国和大秦帝国就是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你说的帝国是哪个?撒哈拉沙漠的生态和亚马逊雨林的生态完全按两种运作模式,你说的又是哪个?我最恨这种没文化装有文化,来哄骗我这种不讲文化的。
真正高级的文化是阴阳,两者得兼,动态平衡,相互成就;非此即彼,因此失彼、水火不容,搁哪都是低端思维。
问题是,怎么个得兼法呢?生态学术研究,在我看来,不应该停留在告诉manager开放创新很重要、松耦合很重要,又或告诉它们控制很重要、价值捕获很重要,而应该告诉他们在何种情形下应该此,何种情形下应该彼,而彼此在同一情景下应如何结合。
粗略一想,有两种思路,分别基于权变理论和动态战略观
权变理论的思路在于找出边界条件
在对话中,主持人问Peter,为啥IBM的生态失败了而ARM的生态成功了。这个问题本身有问题,咱们不展开。Peter的回答是,做生态得找到那个Keystone,IBM没找准,ARM找准了。指的是IBM发明PC把总线技术当控制点后来被Wintel俩小弟翻盘的事儿,而ARM靠IP把握了产业瓶颈。
像ARM这种,有剑桥的科研底蕴打底,手握的keystone够solid, 那就放心搞开放创新,几千个人的小公司能撬动万亿产值。
但这种策略在以开放标准为特色的互联网行业,就不适用了。所以互联网企业找的keystone是啥呢?就是各种投资收小弟、利益捆绑、增加转移成本,等等。玩儿惯了流量虚拟经济的让扎扎实实做冷板凳科研,够呛。
华为按说底蕴够强,开放创新靠谱不?不靠谱。
因为华为强在电信行业,电信行业近百年来是一个封闭的行业,人才基本上集中在几大设备商和运营商(贴金)。你开放基本上就等于开放给竞争对手,外人也不懂你们那么高大上成体系的规范。ARM所在的是IT行业,IT行业没有互联网行业那么开放,但人才资源池有一定通用性。
这就是一个不同行业属性决定不同生态战略侧重点的思路。类似于行业属性这样的东西,通过研究还可以提炼出很多。
比如,我上一篇文章谈到,两种情况下创新者没法依靠外部创新。
一是你的创新技术上太牛逼,根本不存在外部配套,比如爱迪生当年发明电灯,顺便也要发明输电系统;贝尔(at&t)发明了电话电信设备也自己造;IBM搞360大型机必须上全套;一是你的创新模式上太牛逼,牛逼到没朋友。什么意思呢?你的模式与朋友们的既得利益都冲突了,大家都不愿意和你玩,感兴趣的去看看我上一篇文章
最后,fundamentally,地理条件也是一个边界条件。Peter和Arnoud的生态思想(以及清华大学戎珂老师,我同门师兄)是在剑桥培养出来的,基于对ARM的观察。他们都注意到,这种创新模式不同于硅谷。而我的生态思想,底色是十多年在中国产业界的观察和实践,和ARM又生分了。
所以,边界条件是重要的。学者不太愿意谈论边界条件,因为这使得他的研究看起来“狭隘”。告诉大家一个招,遇到这种情况,多留一下学者的成长背景和其理论开发过程(不是理论本身)。
动态战略观的关键是在运动中击破边界
回到我们的问题。我问的是:为何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观察到生态既越来越开放又越来越封闭?生态如何平衡封闭与开放的挑战?
理论上,其实我问Peter那个问题时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下午提交的一篇论文正好讨论这个问题。
任何面向单一领域的创新,无论基于内部或外部,随着时间推移都将日益常态化,创新性降低,松耦合也越来越紧,从做饼(价值创造)转向(价值捕获),最终生态进入成熟期。要扭转局面,企业将不得不不断主动出击寻找新领域,在新领域发展新生态、新合作伙伴、新蛋糕
也就是说,单一业务领域的生态,不可能实现开放和封闭的平衡。企业发展寻找新领域这不是什么新论,但从“关系老化”和生态创新力降低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有些新意。由此引发的思考,不是如何在内部资源分配时如何实现组织的二元性,而在于"如何激发生态合作伙伴的潜能,共同走向未来"
在此过程中,生态主与生态合作伙伴之间不断衍生出新的关系,同时又引来新的合作伙伴,从而维持生态整体的创新活力。这就好比,一股汤炖了太久,都快糊了,创新因子都固化了,这时忽然加入清水(新的市场机遇),创新因子因而重新活跃起来,寻找新的重组互动机遇,间或大厨再加点香料,那味道更胜从前哇。
说这么多,其实就是我的一贯观点。生态用动态的观点看才有意思,动态必然要破界,所以公司生态才是企业持续发展之道。
从合作伙伴的角度,我管你是生态还是帝国,我跟着你干,有发展前途是王道。我这个思路,才是生态主应该向合作伙伴讲的大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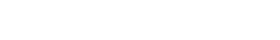
登录 后即可参与评论